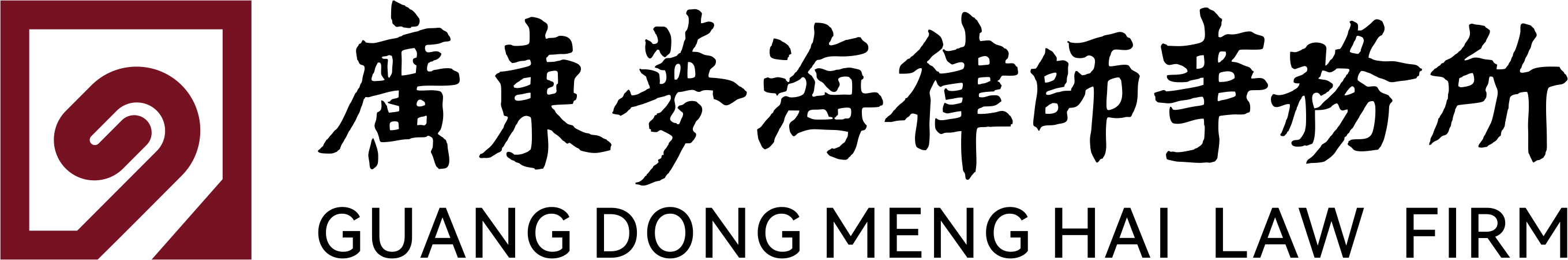法律场域与媒介审判(一)
评书中有一首定场诗这样写道:“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由于种种原因导致的此类现象,使得公民逐渐倾向于寻求媒体和舆论的力量。不难发现,近几年媒介审判现象愈发严重,亟需寻得一种切实有效、具体可落实的规制方式。同时,由于媒体与舆论还具有正面的监督作用,故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来杜绝此类现象。对此笔者拟引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试图通过构建一个新场域来引导舆论、打通民意表达渠道,同时通过新场域内辩论的深入来逐步消解舆论,最终在保留民意诉求的基础上,解决舆论压力问题,保证了司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进而推动法制的完善以及法治的实现。
引言
舆论(public opinion)一词由“公众(public)”与“意见(opinion)”构成。“舆”对应的是公众,“论”对应的是意见。陈力丹认为,“舆论是公众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种评价。”[1]现代舆论的力量主要表现在:首先,舆论是一种对权力以及政治的制约性力量。其次,舆论对立法来说具有推动作用。再次,舆论实现的是普遍的社会监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舆论也越来越倾向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监督权力。当这种社会监督权超越其应有的界限而对司法运行产生了相关影响,就会出现“舆论审判”现象。同时,由于公众信息获取渠道有限,舆论的形成通常会受到媒介的引导而去干预司法,这便是“媒介审判”,此时的舆论便成为了其工具。
“媒介审判”(trial by media)一词滥觞于美国,是指未经过法律程序,即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层面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trial by newspaper)。国内学者则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所作的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是媒介利用其公开报道或评论对司法公正的干预和影响,是媒体新闻竞争日益激烈的产物。”[2]贺卫方在《传媒与司法三题》一文中指出,媒体如果超越了舆论监督的合理界限,会侵犯到司法的独立性[3]。徐显明在“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社会舆论对司法案件做出的“裁判”会使法官承受双重压力[4]。顾培东在《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一文中提出了“传媒审判”一词,认为“传媒审判”的存在是对传媒行为进行必要约束的依据[5]。
有学者将国内对媒介审判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研究兴起阶段,即基于“张金柱案”、“蒋艳萍案”等案例引发的对媒介审判的学术讨论。陈力丹在《200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中指出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所存在的问题,点明了媒体在舆论监督时所做出的越位行为,以此说明媒体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隐含着“媒介审判”问题[6]。魏永征对“媒介审判”的概念作出了较为完备的定义——“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7]
第二,多元化研究阶段,即围绕“孙志刚案”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周泽在发表的《舆论评判:正义之秤——兼对“媒介审判”、“舆论审判”之说的反思》中指出,舆论影响司法这一观点不合逻辑,舆论是对司法是否公正的一种检验方式[8]。史忠治与王忠伟在《中国有“媒介审判”吗》一文中首次对中美两国媒介审判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此阐释了中国媒介审判的独特性[9]。
第三,新视域研究阶段,因网络的出现使得媒介审判产生了一系列新特点。在第三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上,路鹃就《大众传媒时代如何理解媒介审判》[10]一题做了演讲。孔德钦、陈鹏于两位学者发表了《网络媒介审判的负面效果成因》一文,认为网络的匿名性特征会导致集体无意识,从而引发从众心理,最终形成网民的集体狂欢[11]。
新闻传播学界与法学界对媒介审判都开展了一定的研究,但研究方式趋同。同时寻求的解决方式也趋同——相关论著的解决方式大多是对司法机关、媒体、公众三方分别提出建议,忽视了具体建议的可操作性。此外,相较于新闻传播学界,法学界对此议题的研究较少且多借用传播学架构,重视程度不够,创新能力不足。鉴此,本系列拟从场域理论的视角对刑事诉讼中的媒介审判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媒介审判的界定与理论选择
(一)媒介审判的狭义与广义之分
无论是新闻界还是法学界,普遍都是从较为微观的角度来对“媒介审判”进行定义的,对媒介审判的理解较为狭义。主要有两个局限性:一个是对象的局限性;另一个是阶段的局限性。关于前者,当下大多数观点都认为媒介审判影响的对象是审判者,是法院,却忽视了对法庭上的另外两方——控方与辩方的关注。这种狭义的理解直接导致的是对媒介审判影响路径的认知不足。至于后者,部分观点认为媒介审判只存在于庭审过程中,但是庭审前与判决后同样是司法机关与媒介、舆论发生冲突的重要阶段。这种观点的片面,会导致对媒介审判影响利弊的认知不足。定义的片面自然会导致措施的不当,进而摧毁整套理论。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媒介”也并非具体指涉某一媒体,而是泛指一个平台,“媒介审判”并非具体的某一行为,而是指设的一种现象。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对媒介审判作出如下较为广义的定义:媒介审判是指在司法运行的整个过程中,媒体通过引导舆论直接或间接地对法庭内外各方产生影响,最终影响到整体法制的现象。这里所说的整个过程包括庭审前、庭审中与判决后;法庭内外各方是指不仅包括法庭内的控、辩、审三方,还包括法庭外的学界、普通公众等。
(二)选择场域理论的思维进路
对于媒介审判现象的分析工具,笔者经历了以下的探寻历程:先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阿列克西对哈贝马斯的评述次之,最后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哈贝马斯对公众舆论做出过如下定义:“只有两个交往领域通过批判的公共性作为中介联系起来,才会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公众舆论。”[12]公共舆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意见,而某种意见在满足了一定标准的前提下即可形成公众舆论。其标准包括:该意见产生于公共领域;意见在公共领域的内部与外部之间获得了充分的交流。这里包含了哈贝马斯提出的两个重要的理论——公共领域理论与真理共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以市民社会为代表的私人领域与以国家机关为代表的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交集。在这个交集中,市民对某一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并由此形成趋向一致的意见。而该公共领域的意见又会与其他公共领域形成的意见相碰撞,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这在哈贝马斯看来极为重要,是因为普遍的共识即为真理,这也就是真理共识论。但是其形成条件是极为苛刻的,要求其处于一种理想的言谈情境,即“既不受外界偶然因素的干扰,也不受来自交往结论自身之强迫的阻碍”[13],显然这种对机会与能力要求都很高的“理想的言谈情境”是极难实现的。阿列克西对哈贝马斯的这一系列理论进行了研究评述,在一般证立规则的基础上归纳出了三个理性规则与两个证立规则,分别为:包括平等权利要求,普遍性要求与无强迫性要求的理性规则;以及包括可普遍化原则与可检验原则的证立规则。除此之外,阿列克西还提出了其他质疑,如哈贝马斯在真理共识论中并没有提出“真理”的判定规范,同时也未对这些缺陷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现实的操作说明,等等。
布迪厄曾说:“一旦论述科学实践的话语取代了科学实践本身,后果会不堪设想。”[14]可见一项理论能够应用于实践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实现。为此,笔者引入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试图通过该理论中的场域(field)、资本(capital)、惯习(habitus)三个维度来对公共领域理论进行修补并提出实践的可行性方案。场域理论中的“场域”“惯习”“资本”,对应实践中的“空间”“逻辑”“工具”。并且,场域中对抗与反馈的特点为关键所在。具体来说,由于自身惯习的驱使以及对某种资本的追求,使得不同的场域之间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对抗斗争,而在此过程中又不断地将信息进行反馈,从而推动惯习的调整。作为社会实践逻辑的惯习,进一步将该变化反应给所在场域,使得接受重塑的场域能够更好的在场域间的斗争中获取资本。这种螺旋式的上升机制实质就是对真理的追求,这种动态的反馈调整式上升可以弥补哈贝马斯真理共识论中真假确定标准的缺陷。而在内部,资本、惯习、场域三者相互影响——场域制约资本,决定了资本的价值,资本又反过来制约场域,不同的资本类型形成了不同的场域;场域制约着惯习,型塑着惯习,惯习反过来建构了场域,是主观能动应用于客观实践的表现;资本内化了惯习,惯习是实践者身体化了的文化资本力量,从内部对资本施加影响。三个维度相互影响与反馈的循环机制,可以在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吸纳实践者,最大程度地给予实践者参与的机会。同时,三者的相互影响又可以不断地对实践者能力进行塑造与提高,从而提升场域内所达成共识的宽度与深度。这也间接的实现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理想的言谈情境”,在弥补了缺陷的同时达到了实践的目的(如图所示)。

未完待续
[1]陈力丹:《关于舆论的基本理念》,《新闻大学》2012年第5期,第7页。
[2]商登珲:《新媒体视野下媒介审判与司法公正的博弈——以“药家鑫案”为例》,《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81页。
[3]参见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第24页。
[4]参见王好立、何海波:《“司法与传媒”学术研讨会讨论摘要》,《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77页。
[5]参见顾培东:《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第20页。
[6]参见陈力丹:《2001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新闻界》2002年第2期,第10页。
[7]魏永征:《新闻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8]参见周泽:《舆论评判:正义之秤——兼对“媒介审判”、“舆论审判”之说的反思》,《新闻记者》2004年第99,第6页。
[9]参见史忠治、王忠伟:《中国有“媒介审判”吗》,《青年记者》2008年第27期,第87页。
[10]参见路鹃:《大众传媒时代如何理解媒介审判》,中国传媒大学第三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2009年4月25日,中国北京。
[11]参见孔德钦、陈鹏:《网络媒介审判的负面效果成因》,《新闻世界》2010年第2期,第87页—第88页。
[12]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13][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14][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作者:修扬
邮箱:xiuyang92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