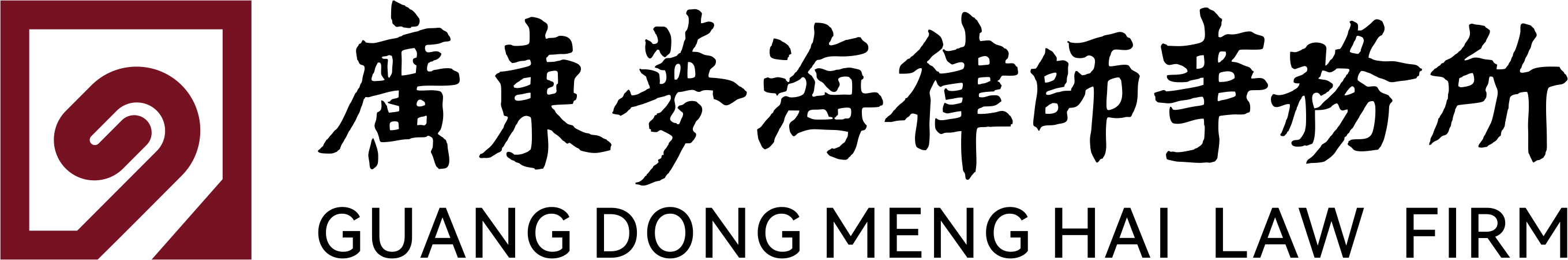时事评论: 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惩治“坏孩子”有待商榷
引 言
近期,关于未成年人两个案件的发生,让人扼腕叹气、愤怒不已。一则为“祖父埋婴案”,二则为“13岁邻居强奸杀人案”。前者的发生呼吁着人们对未成年人关爱程度的加强,而后者的出现却反之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动摇了社会民众对未成年人关爱的信念。从社会民众的传统观念来看,未成年人群体因智力、体力、财力等各方面存在限制或不足,而通常被定义为“弱势群体”。人性本善决定了“关爱未成年人”为社会民众的普遍共识,而这一共识也已融入社会规则之中,成为社会道德的要求,同时也体现在国家法律之中。由于关爱不但包括对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的保护,同时还包括在未成年人侵害他人时对未成年人的宽恕。然而,当社会民众所认定的“弱势群体”中的个体残害他人时,当现有法律无法对施暴者予以“同态复仇”般的惩罚以满足人们朴素的正义观时,这种反差让社会民众无所适从。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因此,当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时,若未满14周岁,无论其主观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抑或是过失,均无需对其行为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果承担刑事责任。此时,相对于该未成年人而言,“最坏结果”则是政府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至于由政府收容教养,则必须额外需满足“在必要的时候”。然而,当未成年人实施恶性案件频频曝光之时,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强烈呼吁“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引入我国刑法规范体系,以突破惩罚“坏孩子”的客观法律障碍。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判断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方式之一。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推定一定年龄段范围内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但如果控方举证证明特定未成年人在实施严重不法行为时具备“恶意”,意识到行为的错误性且故意为之,则该推定可以被推翻。此时,行为人虽未达到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但“恶意补足”后,其则需对其实施的严重不法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简而言之,“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就是通过对低龄未成年人主观恶意的补足,从而形成弹性化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以对实施严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低龄未成年人进行惩治。
1.法律以社会为基础,故法律理应回应社会诉求。“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引入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当下人们惩罚“坏孩子”的朴素正义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与现有规范格格不入,同样会引起诸多矛盾与冲突:生老病死、新旧更替的社会规律决定了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希望,同样也是民族的未来。故而,给予特定阶段的未成年人以宽恕,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故而,我国分别于1991年、1999年先后制定《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实现对未成年人进行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的同时,也在强调对未成年人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挽救方针。
2.人性中对弱者天生就有的悲悯之心,决定了对未成年人以保护、宽恕,也符合社会民众的道德要求。自古以来,我国便有“恤幼”的传统。作为我国封建刑法典范的《唐律》中就曾规定有“十五以下收赎、十以下上请”的条文,该文内容被一直沿用至清代,成为我国传统刑法中体现对未成年人予以宽待的基本准则。故而,“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我国的刑法传统。同时,对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通过“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施以惩罚,又是否引起其他部分社会民众的“恻隐之心”,从而引起修法的反复?
3.相对于其它部门法而言,刑法最为可贵的品质,莫过于具备谦抑性。在当今民主社会,刑罚惩罚后果的严重性决定了刑法适用需具备严苛性。故而,在其它社会关系的调整方法具有良好的调整效果时,社会统治者不应当以刑法的适用作为“急先锋”。
4.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第6条第2款之规定,“缔约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生存与发展”,而我国作为缔约国,对未成年人的权益进行保护已然成为一项国际义务。该法律义务的履行状况,通常也会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的重要指标。
5.该规则的适用成为评判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该行为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重要机制。然而,达到触发“补足年龄”阈值时“恶意”的认定标准却具有高度主观性。这也将导致在同一事件中,可能会导致认定结果因裁决者的不同而截然相反。故而,贸然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将“年龄”这一客观标准变更为“恶意”这一主观标准,等同于将特定境况下的司法公正完全寄希望于每一位裁决者都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和完美的道德品质。在法治中国仍处于进程中的今天,该规则所带来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也许并不如想象般美好。
其实,社会民众最为反对的是“坏孩子做坏事无惩罚”,而非无刑罚。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之规定,对“坏孩子”的惩罚:一则为“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二则为“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其中,针对第一种措施,惩罚主体的特殊、惩罚方式的轻微均使得其在社会民众心中丧失惩罚的意味,更多的则是教育方式;针对第二种措施,“在必要的时候”标准具有模糊性,也更加使得收容教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低,而这也就引发了普通民众对我国刑法所设置的刑事责任年龄标准过高的质疑。故而,基于保护未成年人长远利益的考量,理应在法律规范或相应司法解释层面上对“在必要的时候”的标准进行充分的明确,以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对此标准的确定,理应结合未成年人所的实施危害行为在客观层面上所造成的后果、实施危害行为时的主观罪过、未成年人家长或监护人的监护能力、未成年人生活所接触的社会环境等进行综合考量,并对考量结果通过量化表的形式来实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同时,还应当在相应法律及政策层面上,加强收容教养制度与“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严加管教”的衔接,完善彼此之间相互转换机制的构建,以促使未成年人接受监管和教育的积极性。例如,针对家长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未成年人抗拒监护等情形,应当细化相应标准,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是否对该未成年人转而适用收容教养制度。同理,针对在收容教养机构表现良好的未成年人,应当细化相应标准,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是否对该未成年人转而“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严加管教”。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可以说,我国未成年人群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必然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因此,从国家发展大局的角度来看,对未成年人相关利益进行有效保护,则可为国家相应发展战略的实施不断地提供有担当、有能力的优秀青年。因此,除对“坏孩子”施以宽容和惩罚之外,还理应注重对未成年人价值观念的引导,从而在根源上降低“坏孩子”出现的概率。毕竟,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源头规制,远比事后惩罚要来得更有价值一些。